国语运动健将钱玄同
作者:王昀
——國語運動人物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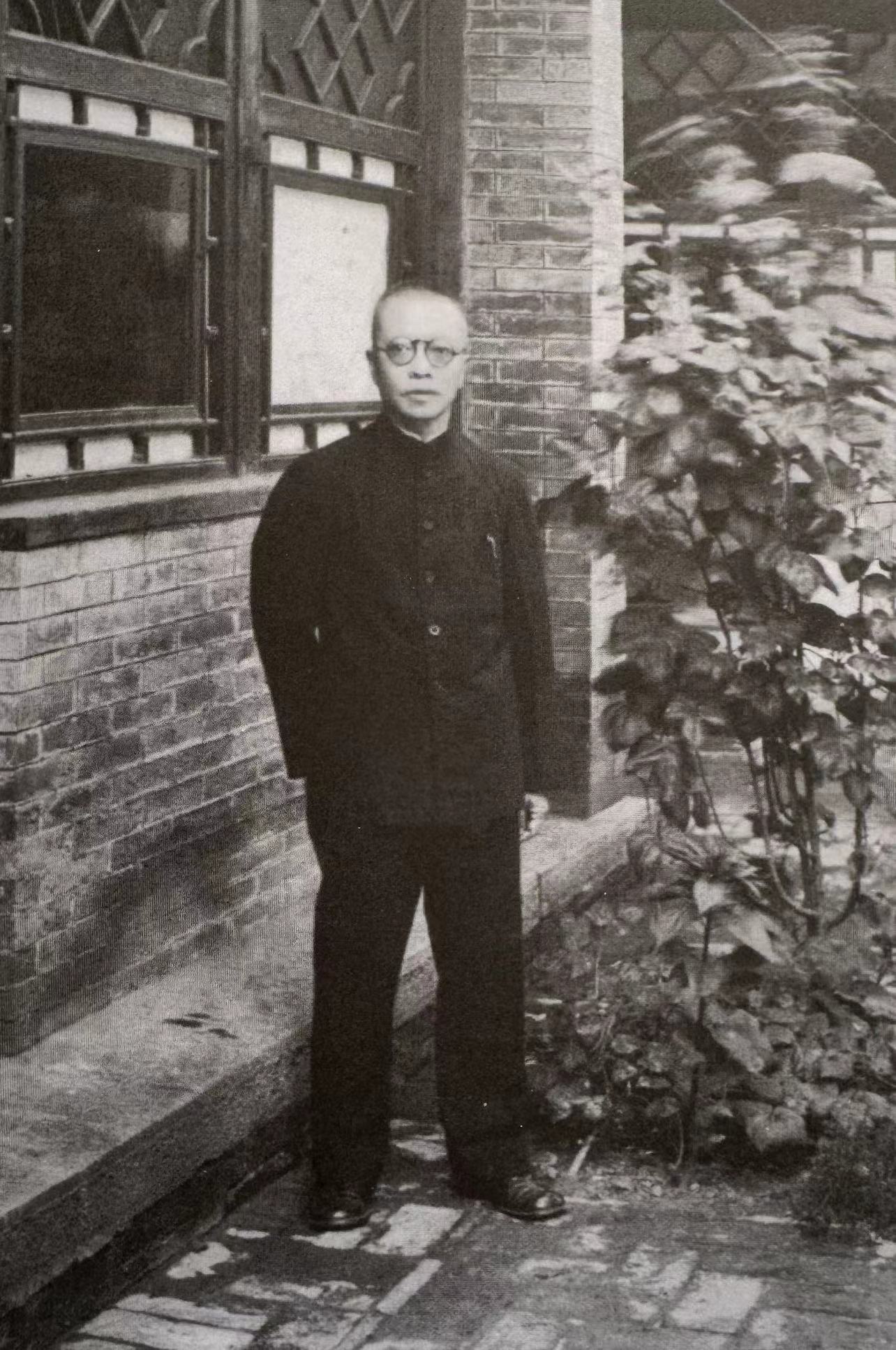
(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玄同在北平寓所)
錢玄同先生是國語運動的領導者,他最大的魅力在于他鮮明的個性。他曾複古,後來則疑古、反古,他因為信仰甚至數度更名。錢玄同原名師黃,字德潛,其父為清同治舉人,後任紹興、揚州、蘇州書院山長,其兄是清末外交官,曆任清駐日、英、法、德等國參贊或公使。受家庭影響,錢玄同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少年的他是一個十足的保皇派。17歲,他讀了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鄒慰丹的《革命軍》等書,開始把“排滿“當成唯一的天職。18歲,梁啓超發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特舉出清學者劉繼莊(字獻廷),說他“最足以豪于我學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二曰倡地文學”,錢玄同讀後對劉氏之學很感興趣,就將自己的號改為“掇獻”,這似乎預示他將成為語言大師。21歲,在日本讀書的錢玄同加入了同盟會,並改名為“夏”,因“夏”在《說文解字》中的解釋是“中國之人也”,以示他對滿清的痛恨。30歲,改名玄同,35歲,在古史辨運動中開始使用“疑古玄同”之名,52歲,病困于淪陷區北平,他又恢複了“夏”的名字,拒絕僞聘至離世。
錢玄同被譽為國語運動健將,他很早就提出要規定中文語法詞序,小學課本、新聞紙旁加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標點符號,用阿拉伯碼號和算式書寫數目字,用公元紀事,書寫方式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下等。他自33歲就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常駐幹事以後,全身心投入國語運動,他鮮明的個性也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他所領導的這個運動中。按錢玄同的計劃,國語的變革是先推行簡化字治中國的“標”,最終要取消漢字治中國文字的“本”,這其實是他給出的國語變革的路線圖。他認為作為語言符號,最重要的是簡單,依聲造字是最科學的,而漢字恰是阻礙中國發展的根源。推行注音符號只是“言文一致”和普及教育的手段,真正的革命是國語羅馬字,即以國語羅馬字來取代漢字,而不是像今天的漢語拼音仍然只起到注音的作用。錢玄同認為,只有當以最少的時間完成認字和寫字,人們才能解放出自己的時間去從事科學的學習和研究。他反對讀經和使用晦澀難懂的各種典故,主張白話文,有骈有散,順其自然。1918年的他一拳打倒了“孔家店”,這不是說孔子要不得,而是反對中國千年來借孔子招牌實現個人目的,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反對個人崇拜。錢玄同當年在《新青年》上說話最痛快最直接,總是特別使人興奮,被推為新文化運動的揭幕人。
錢玄同的激進體現在很多事上。他曾在1925年的國語運動大會上喊出三句口號“打倒古文!打倒漢字!打倒‘國粹‘!”1928年,北伐成功,南北統一,首都遷往南京,大總統府(即中海居仁堂)辟為文化學術機關區。錢玄同主張一定要把剛成立的大辭典編纂處搬到那裏,而其他人則把眼光放在南遷後原教育部所在地。錢玄同說:“既是咱們大規模的‘總糧台‘(注:黎錦熙說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是建設中國新文字的糧台),豈有不和國立北平圖書館並立在中海之理?“那時圖書館撥定的地址正是居仁堂,後來才搬去北海邊的文津街。于是錢玄同和黎錦熙四處奔走,終于由戰地政委會批准國民政府劃定居仁堂西四所為編纂處辦公地點。1926年,數人會提出的國語羅馬字經反複爭議通過後,當時的北洋政府不肯予以公布,數人會請到梁啓超去說情也無果,大家一籌莫展。錢玄同想得一計,不 不使用正式部令,就以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的名義直接布告,把”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正式公布並印成冊。1928年,中華民國大學院(注:當時的教育最高機構)正式公布了國語羅馬字,所以國語羅馬字公布過兩次。
錢玄同是音韻學專家、章太炎的高足,章太炎先生都稱贊他“長于小學”。錢玄同認為中國的語言文字學比傳統“小學”範圍廣泛,應分為四部分,一為聲韻,二為形體,三為義訓,四為方法。他晚年對于“國音符號”的統籌制定頗自負,常對黎錦熙說“非他辦不了,因為古今音韻沿革的研究即是他的專業,又了解全國各地的方音異同。。。”。錢玄同是個實幹家,終其一生,他參與了1918年公布的39個注音字母的討論工作以及1920年正式頒布的《國音字典》審音工作。《國音字典》第一次統一了漢語讀音,意義重大但缺陷甚多。錢玄同在該字典頒布後的第二年又牽頭完成了《校改國音字典》並出版。此時,京音國音之爭正酣,到1923年才算達成一致。錢玄同馬上提案組織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其成果名為《國音常用字彙》,由他親自主編,于1932年出版,被教育部規定為推行統一讀音的字典,替代了原《國音字典》。其間,在錢玄同等人提案推動下成立了“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會中五個北京的代表(包括錢玄同在內)為“數人會”成員,他們是一個討論音韻學的學會,經過二十幾次會議,創造出了國語羅馬字。錢玄同為推廣國語羅馬字大力宣傳,他還親自擔當了國音字母講習所的所長。1928年,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正式成立,錢玄同與黎錦熙同任總主任,按“依史則”原則組織了一個龐大的系統,用五年時間,完成了與《牛津英語大辭典》相當的剪錄搜集工作。1934年,錢玄同提出了《搜采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他于1925年就起草了《第一批簡化字表》,計2300余字,後經南京教育部簡體字會議討論通過了1230余字,最後有324字作為第一批簡化字並公布,但當年簡化字的推行收效甚微。國語羅馬字于1943年被更名為“譯音符號”,功用僅為譯音,這與錢玄同的理想相差甚遠,但國語羅馬字卻成為多年後公布並使用的漢語拼音的雛形。不能不說,國語運動的每一步都包含了錢玄同的心血。
在國語運動中,錢玄同始終堅守著嚴謹和專業的學術態度。1928年冬天,北平大學區成立,致電中央問“北平”二字的譯音,教育部回電說應拼為“peiping“,這與國語羅馬字不合,錢玄同大為氣憤,給時任教育部長蔣夢麟寫信提出抗議,他說:”羅馬字母在學術上、文化上早成為世界公用的字母,制定中國國民的讀法拼法,把本國的名稱寫成拼音文字的形式,其事尤為切要,此與另譯英文名稱,用意全然相反。。。國語羅馬字早已明令由政府正式公布,‘北平‘應拼作Beeipying。堂堂教育部應當做全國運用國語羅馬字的典範,豈能鬧這樣的笑話?”
錢玄同是實事求是的,並不固執己見,在京音國音之爭中,他本是站在“國音”一方的,卻因為一件很小的事轉變了看法。1921年夏,他在黎錦熙家院子乘涼,討論當時小學生正在使用的所謂多數表決産生的“國音”(注:“國音”並不是任何一個地方的讀音,完全是依字由讀音統一會成員投票産生的)讀國語,在全國任何地方都覺得別扭。他說,前幾天他給馬衡家裏的小學生寫墨盒蓋兒,用注音字母拼寫“國音“墨盒兩字,小孩子都說拼錯了,跟日常口語說的不一樣,馬衡也說這兩個字的韻母應該調換一下。他原是反對“京音”的,現在卻反問支持“京音”的黎錦熙:“把北京的地方音作為國音,你以為如何?”黎錦熙答曰:“先生,一個墨盒,你于‘言下大悟’了!”從這以後“漂亮的北京音“成為了日後中國普通話的標准。1933年,在與左翼進行的“拉丁化”論戰中,他雖然對“拉丁化”不感興趣,但肯定了左翼“大衆語”初期的“手頭字”運動,只是認為這應叫做“簡體字”。他曾在1922年發表的《漢字革命》一文中提倡寫“破體字”、“白字”。他分析了漢字的造字方法,所謂“六書”演變過程,至遲從甲骨文以來就有大量假借字,書上的例子不勝枚舉,社會上流行的也有許多 ,如藥方上把“人薓”寫成“人參”,夥帳上把“百葉”寫成“百葉”,“麫包”寫成“面包”等。其實,秦漢時的草書後來不少發展成宋元以來的簡體字,而民間的通俗文學,刊印時使用簡體字的更多了。他後來制作的簡體字表,很多來自于這些字,絕非憑空造出來的。在主張國語統一的同時,他主張要調查方言土語,因為國語既然不是天生的,要靠人力來制造,那就該旁搜博取,他希望多用方言做文章,文學中一但用得多了,就有價值和勢力了。他以為語言愈混合,則愈龐雜,愈龐雜,則意義愈多,意義愈多,則應用之範圍愈廣,這種語言文字就愈有價值。
錢玄同富有一種特殊的幽默感。清廷崩潰時,錢玄同以為正是光複漢族舊物的時候,他參考《禮記》“深衣”說做了一部《深衣官服說》,並照說做了一身衣服。當時他在浙江教育司上班,他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帶”去辦公室,贏得大笑,傳為笑柄。那時,仇滿的他是個複古派。當年《新青年》提倡文學革命時,沈悶的中國思想界既沒有多少人贊同,也沒有多少人反對,新舊思想沒有交鋒,不利于把新文化運動推向前進。于是作為編輯的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給《新青年》的編者寫了一封信,把自己裝扮成反對新文化運動的頑固派,曆數新文化運動的罪狀加以攻擊,劉半農則寫了《覆王敬軒書》,針鋒相對地逐一加以駁斥,兩人演了一出雙簧戲,故意造成一場論戰。錢玄同的信是這樣開頭的:“某在辛醜壬寅之際。有感于朝政不綱。。。歸國以後。見士氣囂張。人心浮動。道德敗壞。一落千丈。青年學子。動辄诋毀先聖。蔑棄儒書。。。”(注:原文仿古文無標點)劉半農回信開頭就說“來信大放厥詞,把記者等狠狠教訓了一頓。。。”結果,這一來一去,引發了文學革命之反響。一位自稱“崇拜王敬軒者”來信指責《新青年》,又有署名者出來為桐城派鳴不平。錢玄同再以記者身份回擊,終于引得桐城派元老林纾出來力挽國粹,抵抗新知。林纾作了一篇小說《荊生》登在《新申報》上,以小說人物影射錢玄同、陳獨秀和胡適,對這三位新文化領袖恨之入骨。後他又寫一小說《妖夢》,影射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還指責起了北京大學成了破壞舊道德的淵薮。不久,在錢玄同的鼓勵下,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掀起新文化運動的高潮。
在國語運動的學者中,錢玄同和許多人一樣,具有很濃的書卷氣。他雖然一生不做政治工作,不加入任何黨派,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思想家。錢玄同認為只有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才是談政治的條件。他畢生從事國語運動,就是為了喚醒民衆。1932年,他在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對社會上一些人空談政治、不幹實事表示擔憂和不滿:“我近來覺得‘各人自掃門前雪’主義,中國人要是人人能夠實行它,便已澤及社會無窮矣。譬如一條街上有十家人家,家家自己掃了他的門前雪,則一條街便已無雪矣。要是雪已掃完,則管管他家的瓦上霜尚可,若放著自己家的門前雪不去掃它,而忙于拿梯子去扒上他家的屋上去刮霜,無論他家討厭不討厭你,總有些無謂:因為自己的門前雪尚未掃也。。。。我是喜歡研究‘國故整理問題‘的,又很喜歡研究’漢字改革問題‘的,它們便是我的‘雪’,我從今以後很想專心掃它們。”1918年,錢玄同和陳大齊有一段精彩的關于教育問題的討論。陳大齊寫信給錢玄同說,為尊重人道起見,看見有人吃糞,不可不阻止他。可是現在我們中國苦于沒有辨別力,不知道哪種是糞,須先指點他們才好,因此請錢玄同編個“糞譜“,目的是喚起民衆。錢玄同是國學專家,思想激進,入室操戈,最宜擔當此任,他自小深受舊學毒害,對”糞譜“了如指掌,對”糞學“恨之入骨,他回信說:”‘糞譜’雖然是個滑稽的名詞,其實按之實際卻很確當。因為今天名為糞的,實是昨天所吃的飯菜的糟粕,昨天把飯菜吃到胃裏,其精華既然做了人體的營養料,其糟粕自然便成了糞,到今天自然該排泄了。。。但是若不排泄,藏在胃裏,卻要害人體致人生病。照此看來,糞本身原沒有什麽可惡,可惡者,是那些藏糞不泄的人。而且他們不但自己藏糞不泄,還要勸人。。。你想青年和他們有什麽九世深仇宿怨 ,他們竟要用這種亡國滅種的圈套來陷害青年啊!“同年,他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周刊》上發表《施行教育不可迎合舊社會》一文,明確提出教育的目的是教人研求真理,不叫人做古人的奴隸;教育是教人高尚人格的,不是教人幹䘵的;教育是改良社會的,不是迎合社會的。作為語言文字學家,錢玄同認為漢文是一切舊思想的軀殼,必須堅持廢除:“大抵中國人腦筋2000年沈溺于尊卑名分綱常禮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驕“”谄“二字。富貴而驕雖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貧賤之時,苟遇富貴者臨于吾上則趕緊磕頭請安,幾欲俯伏階下,自請受笞,一若彼不淩踐我,便是損彼之威嚴,彼之威嚴損則我覺得沒有光彩者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複拜跪,仔細想想,豈非至奇極怪之事。”他犀利地把舊文學與舊體制、舊思想相聯系在一起。對現實問題也有著自己的看法,晚年他在給周作人的信中說:“我近來覺得改變中國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義。中國人‘專制’‘一尊’的思想,用來講孔教、講皇帝、講倫常。。。。。。固然要不得,但用它講。。。主義還是一樣要不得。。。。。。我近一年來懷杞憂,看看‘中國列甯’的言論,真覺害怕。。。這條‘小河’一旦‘洪水橫流,泛濫兩岸’,則我等‘粟樹’,‘小草’們實在不免膽戰心驚,而且這河恐非賈耽所能治,非請教神禹不可的了。“
錢玄同被許多人認為是偏激的,但他卻並不是一個壞脾氣的人。他個子矮小,很早發胖,被魯迅諷刺為“胖滑有加,唠叨如故”。他生性好說,是個“話匣子”,樂于談天,常說“上課倦了,下課和朋友閑談便立刻振作起來“。他談話莊諧雜出,用自造典故或開小玩笑,聽者不禁發笑,但生疏的人往往不能索解。他稱到朋友家談天叫“生根“,生根的地方有沈士遠、胡適、劉半農、黎錦熙、周作人等人的家。一般是晚4-6點,他提著皮包手杖進了各家的客廳或書房,海闊天空地談起來,時間不夠則相約去”雅“(指上館子吃飯)。如果朋友家有飯吃,則說”某人賞飯吃“。天暖時也會同去中山公園,他謂之為”大雅“,除談國語,也談所見所聞,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周作人說”他對人十分和氣,相見總是笑嘻嘻的。但假如要讓他去叩見“大人先生”,那麽他聽見名字,便會委實不客氣地罵起來,叫說話的人下不來台。他論古嚴格,若和他商量現實問題,卻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中道的人“。他畢生從事教育,桃李滿園,卻不喜歡學生們對他的態度言詞太拘謹。他給學生寫信,每稱對方“先生”,稱自己為“弟”。搞得很多學生誤解,說錢先生不認他為弟子,所以他後來改稱某某“兄”了。魏建功佩服他的這位先生,在于錢先生能超脫流俗而表裏如一地“安素務新,名如其分”,守望禮法而不守舊,求進步而不炫奇,他的偉大在“循循善誘”而“無拘牽墨礙”地引導後輩。
錢玄同一生處于空前的內憂外患中,他痛感中年以上的人多固執而專制,便憤然道:“人到40就該死。。。“1927年他滿40歲時,幾個朋友和他開玩笑,打算在《語絲》周刊裏發刊一期《錢玄同先生成仁號》,最終沒刊行。胡適作了《亡友錢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紀念歌》曰:”該死的錢玄同,怎會至今未死。。。“ 誰知錢玄同最終因北平淪陷封城被困在中海,深夜回家,血壓突高,不幾日竟英年早逝!錢先生終沒能看到他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的幸福“的平凡工作之豐碩成果。只是不知道他”漢字遲早要廢“的理論是否會成為現實,而他的名言應為後人永遠銘記——“考古務求其真,致用務求其適。”
2024年4月11日
參考文獻:
《國語運動史綱》 黎錦熙 商務印書館
《錢玄同評傳》 吳銳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增訂注解 國音常用字彙》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