遜清的國語運動倡導人
作者:王昀
國語運動倡導者多是新思想的推動者,而簡字運動的主導人勞乃宣卻是個名副其實的遜清遺老。1921年7月21日, 勞乃宣在青島病逝,他告訴自己的子女,以前朝一品官服服斂,以表明自己忠清勿忘故君之志。這年元旦,溥儀曾賜寫“丹心黃發”匾額賞予他。
勞乃宣(1843-1921),字季瑄,號玉初,浙江桐鄉人,祖籍山東陽信。同治十年(1871)中進士,曆任臨榆、南皮、完縣、蠡縣、吳橋、清苑等地知縣,曾創辦畿輔大學堂,出任南洋公學、浙江大學堂總理以及京師大學堂總監督。
勞乃宣沒有出洋的經曆,也沒做過大官,但勞家是書香門第,科第不絕。勞乃宣母親的家族同樣顯赫,其母沈蕊知書達理,善作詩詞,著有《來禽仙館詩稿》。由于受母親的影響深刻,以至勞乃宣後來特別關注啓蒙教育。勞乃宣的童年時光,大部分時間與母親的家人生活,他曾在丹徒、震澤、無錫、江甯、蘇州、常熟、泰州、天津、保定等地居住,有過十幾位先生,說著不同的方言,可謂“三裏不同調,十裏不同音”,引發了他對音韻的好奇。他喜歡上射字之戲,這是宋元時期出現的一種以韻圖為依據的語音遊戲。遊戲由兩人玩,一人隨機確定一個字,用擊鼓、拍掌、彈指等方法,按韻圖規則發出幾組不同次數的響聲,以代表不同的語音元素(聲線、韻母、聲調等),另一人通過識別語音元素再進行組合,從而拼出對方想要的字音。天資聰慧的勞乃宣在遊戲中逐步掌握了漢字音韻之理,從此與等韻學結下不解之緣。
1900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出版不久就得到了勞乃宣的關注,他覺得這與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但他認為王照的方案不適合在江浙地區推行,于是他潛心編寫了《簡字全譜》,于1907年在南京出版。書中,京音一譜全依王照方案;在京音五十母外加六母,十二韻外加三韻,創《甯音譜》;再加成六十母,十八韻,成《吳音譜》;最後加至八十三母,二十韻,成《閩廣音譜》,合總一百十六母,二十韻,為《簡字全譜》,包括全國各地方言。勞乃宣主張南人先就南音簡字各譜學習,以便應用,學成之後再學京音,以歸統一。
1905年,勞乃宣陳請兩江總督周馥、江蘇巡撫陳夔龍、安徽巡撫恩銘設立簡字學堂。學堂只授簡字,針對的是貧寒子弟,半日謀生,半日學習,待簡字推廣到一定程度後,識字率提高了,普通民衆可以閱讀書報,通曉時事,普及教育開啓民智就水到渠成。經勞乃宣的努力,簡字教育日益推廣。
此時,關于國語統一問題爭論紛呈,到底是“強北就南”還是“引南歸北”是最主要的焦點。在簡字問題上,勞乃宣被黎錦熙等人認為是王照的“同志”,事實上,王照曾到南京考察簡字學堂,並不贊同勞乃宣的“分兩步走”,還在《中外日報》發表《評勞乃宣“合聲簡字”》的評論,稱“今改用拼音簡字,乃隨地增撰字母,是深慮語文之不分裂而極力制造之。。。”,把分裂漢語言文字的難赦之罪加在勞乃宣身上。勞乃宣則回複:“夫文字簡易與語言統¬一,皆為今日中國當務之急。然欲文字簡易,不能遽求語言之統一。欲求語言之統一,則改先求文字之簡易。”他以為強行推行官話,對南方人無異于學習以表意為主的舊體字。如果天下人都能以方言拼讀文字,即使不懂官音,也是有益的。
經舉薦,1908年5月23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在頤和園仁壽殿召見了忐忑不安的勞乃宣。談及簡字學堂,勞乃宣奏雲:“簡字學堂,簡字就是拼音字母。中國的字難認,所以認得字的人少,小孩兒從小上學,總得好幾年才能粗通文理。鄉下人都沒有能力念書,所以認字的人少,都不能明白道理,教育難以普及。而簡字最好認,念書的人幾天就學得會,不認得字的人頂多用幾個月,沒有學不會的。學會了就能寫信看書,再用這個編出書報叫人看,就能使人人都明白道理。”
皇太後雲:“中國認得字的人太少了,要能叫天下認得字的人變多,那就好了。”
勞乃宣奏雲:“江南辦這個簡字學堂很有成效,聽說直隸、奉天也辦了,其他省還沒有要求。”
皇太後雲:“皇上把這個簡字頒行天下,必叫天下幾萬萬人都認得字,都明白道理,要能如此,天下就容易治了。”
此次,勞乃宣呈遞了《進呈“簡字譜錄”折》,闡明推廣簡字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取得的成效,建議在全國推廣。慈禧太後看後,令學部議奏推行簡字,勞乃宣終于看到了曙光。誰知不久光緒帝和慈禧太後辭世,學部內部對推廣簡字存在分歧,對勞乃宣的上書,既不討論也不奏報。
年底,宣統即位,勞乃宣又看到了希望,次年他再次奏請推行官話字母,並進呈《奏請于簡易識字學塾內附設簡字一科並變通地方自治選民資格折》,表明簡字是推行普及教育行之有效的工具,他再次不厭其煩地陳述英美與日本的拼音工具便于普及和以往取得的成效等,懇請學部討論簡字。雖然他字字懇切,句句肺腑,最終也沒能打動攝政王載沣的心,落了個不議不奏的境地。
眼看朝庭不支持,勞乃宣在北京設立了簡字研究會,他利用自己的關系廣攬人才研究簡字,其中不乏文人學者和學部官員。1910年3月13日,簡字研究會在汪榮寶的石橋別業大院召開了首次會議。
1910年10月,清廷成立資政院,勞乃宣被欽選為資政院碩學通儒議員、理藩部奏派咨議員,他再次利用這個舞台做了最後的努力,積極建言推廣簡字教育。1911年1月,資政院終于討論了簡字報告,提議將簡字切音更改為“音標”,報告獲得大多數議員的贊同。他在發言中闡述自己的主張和向朝廷進言的辛酸曆程,並以“我們中國要有幾萬萬明白的國民,那不無敵于天下嗎?”為結束語。8月,中央教育會議議決《統一國語辦法案》,以政府法案形式把統一國語分為調查、選擇及編纂、審定音聲話之標准、定音標、傳習等五個步驟。至此,勞乃宣為之奮鬥六年的簡字活動終于在國家層面得以開展。然而,一個新紀元的開始,讓這個來之不易的《統一國語辦法案》再次付之東流。
勞乃宣對簡字運動的熱衷源于其對教育的熱愛。他23歲中舉人,有了做官的資格,但卻無官可做,有家要養。這一年他被保定知府博爾濟吉特·恭鈞聘為自己三個兒子的家庭教師。勞乃宣在教授知識的同時,還教育三個孩子要志存高遠,將來成就一番事業。這就是勞乃宣教育生涯的開始。
1884年,勞乃宣在完縣任職時,為當地的燕平書院解決師資和資金,提高教師津貼和學生獎學金,出資購書,使書院學風大振。1891年,勞乃宣在任職吳橋知縣時,同時兼任教谕訓導,擔負文廟祭祀和縣學生員教育的職責。他對士子的教育尤為關切,親自主講瀾陽書院,自購各種書籍藏于文廟中供人們閱讀以開闊視野。他還特別重視與學生的交流,使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在瀾陽書院紮下了根。
1893年,勞乃宣在吳橋任知縣的第三年,他認為對一般百姓的普及教育應當被提上日程。他在吳橋設裏塾,想仿照古代巷闾家塾制度開展民衆教育。他在《勸設裏塾啓》一文中稱:“夫天下秀民少,而凡民多,秀民有教,而凡民無教;則受教之民少,而不教之民多。散億兆不教之民于天下,而欲求世之治也,不亦難料乎。”勞乃宣認為,一個國家要實現自強與發展,只有提升全體民衆的教育水平,“教凡民使人人知為人之道”,才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于是他發動瀾陽書院的士子深入吳橋的城鎮和鄉村進行裏塾制度的調查。考慮到農民的特殊情況,他把裏塾的教學安排在冬季農閑時光,教授《弟子規》、《小學》等淺顯易懂的內容,學生中既有兒童也有成人,教材為免費發放。“這不啻開今日短期民衆學校教育之先河。”(民國學者陳訓慈言)
在1898年,勞乃宣奉命創建畿輔大學堂,這是保定第一所新式學堂,也是中國首批高等學府,與京師大學堂同年。勞乃宣雖是舊式文人,卻清醒地認識到“今日全球交通,西學東漸,笃守舊聞不足以應當世之務”。從課程設置看,中外兼習,設有國文、倫理、經學、英文、數學、理化等課程,引入國外之英文原版課本。他重視師資,解決校舍和學生獎學金,甚至考慮了畢業去向,學校一度聲名鵲起。可惜,該學校于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被燒毀。
1901年春,在上海養病的勞乃宣受邀擔任了南洋公學總理,雖然因身體原因只在任三個月,他提出了留學方案,選拔優秀學生赴英國深造,還建議公學設立政治班、小學堂等,對學校有著積極的影響。年底,他身體康複後就任浙江求是大學堂總理。
1904年,62歲的勞乃宣為兩江總督擔任幕僚,協助周馥在江南大興新式教育:在南京改建擴建多所學堂,將三江師範學堂更名為兩江師範學堂,將格致書院改為農工商實習學堂,成立江南蠶桑學堂、初高等小學堂、教育研究所、商業學堂和¬江甯第一女學堂等。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位把推行簡字、普及教育、提高民智為己任的勞乃宣卻是孔教和清廷的堅守者。1861年,19歲的勞乃宣娶了“千古聖人”孔氏後人孔蘊徽為妻,這被他認為是巨大的榮幸,其思想更是深受孔府影響,也許這就是他“忠君”和“尊孔”的重要原因。
在清末一場後世稱為“禮法之爭”的新舊法律較量中,勞乃宣充當了一個悲情而荒誕的角色。以沈家本為首的法理派和以勞乃宣為首的禮教派爭論不休,而最激烈的爭議竟是“無夫奸”問題。勞乃宣在會上說:“無夫奸,中國社會普通的心理都以為應當有罪,這個道理極平常,沒有什麽深微奧的”。經過反複爭議,最終以法理派妥協退讓而草草收場,新刑律附上五條附則,規定了無夫婦女通奸罪等。 1913年,隆裕太後病逝,71歲的勞乃宣趕赴崇陵,換上清朝臣子的袍褂,在靈前行三跪九叩禮,並伏地痛哭。民國政府外交總長孫寶琦來致祭,著西裝行三鞠躬禮,被勞乃宣等遺老罵得無地自容。
民國後,勞乃宣拒絕任公職。1912年,教育部擬召開讀音統一會,主持此事的吳稚晖親赴涞水邀請勞乃宣,被其婉拒。盡管他迫切希望漢語改革,這是他傾注十年的事業,但他是大清遺臣,斷不參加民國政府的會議。他私下給吳稚晖寫了信,並郵寄了自己的《簡字譜錄》、《等韻一得》、《簡字從錄續編》等,還派自己的女兒勞缃到會旁聽。
晚年的勞乃宣選擇青島為居住地,他做了兩件大事,一是與德國人衛禮賢合作,將《易經》譯成德文。《易經》德文版出版後,著名心理學家榮格作序並推薦,他在序中說:“我不是漢學家,因為個人曾接觸過《易經》這本偉大非凡的典籍,深切體會到他翻譯的《易經》在西方是無可比擬的,在文化上也有相當重大的意義。” 衛禮賢還在青島創辦了禮賢書院,主要是為青島所有的“蒙養學堂”培養教師,為此還被清廷授予四品頂戴花翎。勞乃宣發起的尊孔文社就設在禮賢書院。勞乃宣表明此文社以“尊孔”二字為標榜,其內涵又以孔子之道為實踐的依歸,重視儒家道德修養。辛亥革命後,一群遜清遺老共同聚首于這裏。他們曾憂患清王朝顛覆,再次發生焚書之轍,在尊孔文社內建起一座藏書樓,以最早來青島的傳教士花之安所遺藏書為基礎,加之新購及成員饋贈,總計藏書1.2萬冊。由于尊孔文社有泛精英的特征,一些日本和歐洲學者頻頻光顧。
1917年1月溥儀壽辰之際,勞乃宣去京,與衛禮賢合謀,欲讓溥儀娶德國公主為後,以換取德國對複辟派的支持。這件事在溥儀《我的前半生》中記載著:“勞乃宣悄悄地從青島帶來一封信,發信人的名字已記不得,只知道是一個德國人,代表德國皇室表示願意支持清室複辟。勞乃宣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機緣,如果再加上德清兩皇室結親,就更有把握。“後來,張勳複辟事件,讓勞乃宣成為”逆流“。
在學術上,除了音韻學,勞乃宣對算術還情有獨鍾。1876年,他就曾寫過《筆籌算略》,後又撰寫了《古籌算考釋》六卷算學著作等。1898年,他還編寫了兒童教學的籌算課本《籌算蒙課》,包括算式、列位、加減乘除等內容。
勞乃宣一生做過許多有益的事,1873年,他曾與黃彭年編纂過《畿輔通志》;他曾查辦涞水縣車廠村禮王府圈地案,為村民減租減負;在保定大旱時,與同鄉創建平粥會,賤賣粥給平民;在臨榆任知縣時開門辦公,政務透明,懲治不法庵尼,辦義塾,教養學童。他知識廣博,對外交內政事務均有洞察力。當年,他憑借對義和團特別清醒的認識,以嚴治確保他所治理地區未發生拳亂。
作為國語運動的倡導者和先驅,我們完全不應該忽略勞乃宣為推進簡字運動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的聰明才智,而他雖是一個頗富爭議的人,但卻不失為一個有著自己信仰和追求,值得尊重的獨立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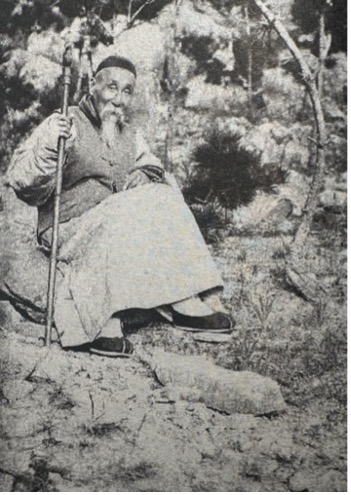
1919年勞乃宣遊崂山
參考文獻:
《勞乃宣傳》 陳勇著 華文出版社 2022年
《國語運動史綱》 黎錦熙著 商務印書館 2011年
